

在思想史领域中,很少有哪个命题能如“启蒙”一般,在历经两百余年的阐释、赞美、批判乃至宣告“终结”之后,依然保持着如此灼热的当下性。不久前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者莫克尔(Joel Mokyr)在其《启蒙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 Britain and the Industrial 1700-1850)一书中,便将启蒙时代思想与信念的深刻变革视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在德国统一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面对德国总理莫茨(Friedrich Merz)提到的“暗黑启蒙”(Dark Enlightenment),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回应以重振启蒙价值的倡导:“我们还有一条通往‘新启蒙’(nouvel Aufklärung)的道路,一条热爱文化、音乐、文学、对话和辩论的道路,一条相信尊重和科学比仇恨和愤怒更强大的道路。”而在中国语境中,“新启蒙”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回声。20世纪80年代,王元化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冻期倡导“新启蒙”,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拾五四时期的理性与科学精神。不同脉络中的“新启蒙”,无不提醒着我们启蒙从未远去。本文围绕《新启蒙札记》一书,澄清与启蒙有关的一些关键性误解股票股指配资,并对新近有关启蒙思想的研究进行了述评。

撰文|李嘉琪(复旦大学历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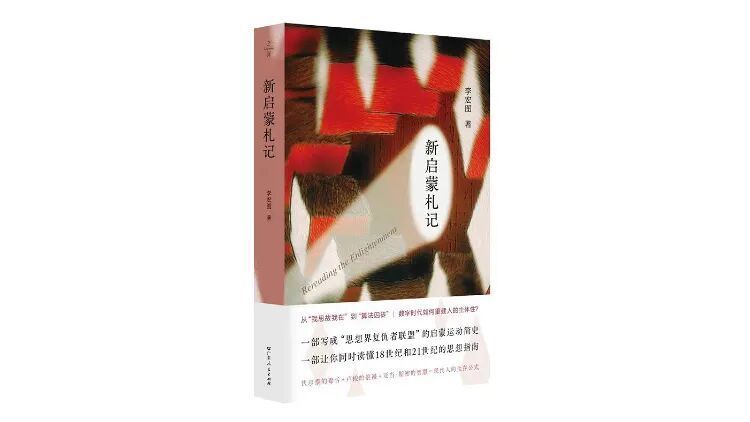
《新启蒙札记》
作者:李宏图
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人的科学”
今天,那个曾以理性、进步与普遍人权照亮现代性的伟大思想变革,似乎正陷入新的危机:虚假信息的泛滥、情绪政治的崛起、算法权力的扩张、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都在不断侵蚀着启蒙所奠定的理性秩序与价值基石。今天的我们或许比十八世纪的人更接近康德所言的“自我加诸的不成熟状态”。由此,“新启蒙”这一关乎当下人类文明走向的现实呼唤显得从未如此迫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欧洲近现代思想史学者李宏图的新作《新启蒙札记》显得格外及时。在书中,李宏图教授通过札记这一更为灵活轻盈、深入文本的形式,重新思考启蒙的精神内核,追问着启蒙的未竟之业:在一个理性失重、价值崩塌的世界中,我们还能如何重新思考启蒙的价值、再一次明晰现代社会的根基,又该如何恢复对理性、科学、进步与人的尊严的信念?
一切探问都必须自“理解”始。正如书中引述思想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所言:“作为启蒙运动的孩子,我们应该努力理解父辈。”基于此,《札记》全书分成三辑,从启蒙的精神内核发轫,再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两种典型样式进行分述,揭示启蒙思想家如何确立自由、市场、法治、平等、博爱、科学等诸多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正与当今国际学界启蒙研究的两大范式转换共振和鸣:一是从“整体”转向“差异”,二是从“单一”转向“多元”。前者意味着不再将启蒙仅仅视为整体性的板块,而是重新关注其内部的裂缝、争辩与多样化的理论实践,例如伏尔泰与卢梭之间的分歧、法国与苏格兰启蒙的差异,恰恰揭示了理性、自由与社会秩序并非唯一逻辑的产物,而是思想博弈的结果。后者则体现出对“复数启蒙”的体认:启蒙不再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单向传播史,而是英、法、苏、意等多地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展开的平行实验与互相激发的思想网络。
正如本书的前言中所写:“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改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精神革命’或‘文化革命’,具有思想解放和确立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同于传统启蒙研究以“理性”为轴心的叙事,《札记》在兼顾了“理性”特质的同时,也将启蒙的内核重新引向苏格兰思想家休谟所言的“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指出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阐发”。无论是康德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宣告理性的自主与批判精神的诞生,伏尔泰高扬“牢记你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人文信条,还是休谟以经验主义哲学将“人”重新置于认识的中心,抑或亚当·斯密通过“经济人”理论奠定现代商业社会的伦理基础;从法国启蒙到苏格兰启蒙,从理性解放到商业文明,启蒙思想在不同语境中展现出丰富的形态,既体现了启蒙的多样性与复数性,也揭示了其统一的精神核心:对人的权利、尊严与幸福的持续思考。
于是,《札记》第二辑首先将目光投向苏格兰,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另一条思想源流。正如文中敏锐指出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属于整个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谱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带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与诞生于贵族沙龙、以抽象理性为旨归的法国启蒙不同,苏格兰启蒙诞生于大学与“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交往空间,其思想根系深深扎根于制度、商业与道德生活之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幸福如何达成,现代社会如何可能?他们并未以纯粹理性取代一切,而是在理性之外承认社会既有的习俗与惯例的力量,更敏锐地意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正因如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与设计呈现出分段与开放的结构,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商业社会”揭示市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平衡机制,弗格森(Adam Ferguson)则以“公民社会”强调个体德性与共同体责任。
亚当·斯密。
由此,《札记》探寻了多位苏格兰思想家何以在理性与情感、个体与共同体、自利与公共善之间,探寻现代社会秩序生成的内在机制。例如,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提出“私人恶德”亦可引导转化为“公共利益”,揭示人性欲望与社会繁荣之间复杂的张力;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中从公民美德与个体责任出发,指出自由不仅是免于干涉的权利,更是公民承担责任、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践;而亚当·斯密则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将情感与理性、伦理与市场融为一体,展示了人类社会如何在“共情”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这些都体现了“人的科学”这一启蒙的核心精神:“人”通过感情的共鸣、利益的权衡与习俗的维系,逐步形成了社会合作与道德约束的秩序。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的交换、信用的维系、科学知识的创造,乃至工厂制度与生产方式的革新,都体现了“人的科学”的多重维度。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场真正以“人”为尺度的社会与思想变革。
启蒙思想的多重向度
与之相对,法国启蒙则以“自然权利”为核心,将“人”的问题置于个人权利的层面进行探讨。第三辑开篇即指出:“对‘人权’的系统性表达和强调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支撑这一核心的理论基础,正是“自然权利”理论。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自然权利”推导出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此需要国家以主权的设立换取生存的“安全”;而洛克(John Locke)则进一步将自然状态中的人描绘为具有“生命、自由与财产”三项固有权利的存在,国家的合法性正是基于保护这些权利的契约。法国启蒙思想家继承了这一自然权利传统,也同时赋予其全新的普遍性与政治使命。
沿此脉络,《札记》从不同维度对法国启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重思。例如,关于伏尔泰的篇章从常被忽视的“安全”维度切入,指出伏尔泰的核心关切,不仅是防止暴政与宗教偏执对个体的威胁,更在于使包括人身、财产、信仰以及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安全”从贵族特权的专属权利,转化为所有公民在法律与制度框架下所共同享有的普遍权利。而对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诸篇细读,既揭示了他以“法治”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构想的现代政治体制,更深入探究其以“人口”问题为切入点,对政治自由与社会繁荣之间关系的洞见:唯有自由,方能激发创造力与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这也与亚当·斯密的主张形成呼应与互证。
此外,《札记》对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整体性特征与“江南”地区以“经济压力”换取“政治宽和”的地方特殊性论述亦作了富于启发的考察。由此看来,自由亦可在社会内部权力、财富与秩序的彼此牵制与调适中显形,而这种地方经验可以成为制度自我更新与未来选择的重要资源。笔至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札记》沿袭了对卢梭的共和主义解读。卢梭揭示了人如何由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转变为社会状态下的“政治人”,从而在契约共同体中实现由“天赋自由”向“公民自由”的转化。由此,“自然权利”在卢梭那里被重新定义为“人民主权”的思想根基;政治的合法性,不再源于君权或传统,而取决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即公民在公共理性的引导下,为共同善而行的普遍意志。卢梭正是以此反思并批判了当时君主专断的政治体制。
正因如此,《札记》特别强调,应当超越将卢梭简单归入“多数人暴政”或“极权主义原型”的误读,回归学理性研究,特别是回到文本之中,重新理解以“人民主权”为代表的关键概念所蕴含的复杂张力。《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轨迹也得到了关注,从以“人民主权”反专制的革命话语,到被纳入自由主义谱系或“公意”争论的学理框架,展现了卢梭思想在在跨语境传播中的重写与再造。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
作者: [美]丹尼斯·C.拉斯穆森
版本: 格致出版社
译者:徐秋慧
2021年5月
除此之外,《札记》也将视野延伸至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d’Holbach)、狄德罗(Denis Diderot)、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等思想家,勾勒出法国启蒙在理性祛魅、知识体系重构与历史进步信念上的多重向度。启蒙精神在他们笔下展现出从个体理性走向人类解放的普遍雄心,也使启蒙的光芒穿越18世纪的欧洲大陆,照见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恒久冲动。
《札记》中的相关内容也对国内外学界及公共语境中的常见误读进行了澄清。以“自然权利”理论为例,书中指出,人们往往将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与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视为同源,误以为三者皆源出契约论与自然权利学说。然而,李宏图教授强调,英国《权利法案》的理论基础并非自然权利,而主要是“沿袭英国1215年大宪章以来的自由传统”。文章指出,条文的开篇即写明:“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而制定”,其核心目的在于划定国王与议会的权力边界。换言之,《权利法案》是为了“恢复”被詹姆斯二世所破坏的“古老权利”,它所列举的权利,如“未经议会同意不得中止法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议会内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以及禁止“残酷和非常的惩罚”,全都被视为英国人自古以来的“遗产”,而非全人类的“自然权利”。
正如波考克(J.G.A. Pocock)在其经典著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中所揭示的,17世纪英国政治辩论的主要“语言”不是抽象哲学而是“历史”。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也认为,英国普通法传统乃至自由观念的形成,部分可追溯至罗马法关于“自由人”(liber homo)与奴隶区分的“新罗马”(Neo-Roman)思想谱系。因此,《权利法案》所确立的是一种基于历史惯例、法律实践和社会经验的自由理念,而非源超历史、自形而上的“自然法原则”。
在理论层面,英国(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边沁等人亦对自然权利学说提出深刻批评,他们指出,将建立在“应然”假设之上的“自然权利”视作超历史的普遍真理,反而遮蔽了权利在具体社会经验中的生成逻辑。这样从文本出发的分析不仅有力地纠正了将三部人权文本视作同一思想谱系的线性叙事,更揭示出启蒙运动本身的多重逻辑:英国的自由理念根植于历史惯例与法治传统,法国的“自然权利”则立足理性与普遍法则,追求政治正当性的重建。
如何理解美国的《独立宣言》?
值得补充的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源流,实际上也并非单纯的“洛克主义”可以概括。首先,文本中以“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替代了“财产权”,这一经典措辞长期被视为对洛克财产权概念的扩展。然而,历史学者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提出了修正观点: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求学期间深受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熏陶,而“追求幸福”的表述也更接近苏格兰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对道德感与公共善的强调,而非洛克式的对物质财产的占有。
尽管威尔斯的论点在当时学界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过度强调哈奇森相对于洛克的重要性之处不无偏颇,但总体而言,他确实揭示出这一表述改变之下的复杂性:杰斐逊的确与哈奇森一样,将对权利的坚定承诺与对情感、道德感的诉求结合起来。正如政治哲学家塞缪尔·弗莱沙克(Samuel Fleischacke)指出:“在承认人类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刻关系的同时,又不否认每个人终究以个体形式度过其一生,这一平衡正是苏格兰思想的独特印记,也是哈奇森传递给其后继者的精神。”无论如何,这一争论确实表明,《独立宣言》文本的思想内核是在一个多元而交织的思想场域中孕育而成。
约翰·洛克。
20世纪中后叶以来相关研究的“共和主义转向”,也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独立宣言》的思想解读。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与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等学者指出,美国革命的思想底色与其说是洛克式的个人权利哲学,不如说更接近十八世纪英国本土“激进反对派”的公民共和传统。约翰·波考克则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提出贯穿英伦与大西洋世界的“共和主义语汇”。在这一视野下,《独立宣言》中关于“人民”“美德”“幸福”的表述,被重新理解为共和主义对公民德性、公共参与与政治自我治理的强调,而不仅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宣告。
此外,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独立宣言》不仅是一份政治宣言,更是一份为争取国际承认而制定的外交文件。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便指出,《宣言》在文本开篇和结尾多处强调独立平等的国家地位的表述,明显使用了18世纪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关于“主权国家”定义的国际法话语。瓦特尔在其《万国法》(The Law of Nations)中指出,“独立”是一个国家成立、取得国际合法性的前提。从这一角度,《独立宣言》正是通过引入国际法语言,来确立美利坚对外的合法地位,而这样的国际法理维度,正是洛克所未曾涵盖的。
如此综合来看,《独立宣言》的思想源流本身就揭示了启蒙的多样形态:既与法国启蒙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自然权利”理念,又在苏格兰道德哲学、英伦共和传统与18世纪国际的主权话语之中完成了具有美国经验的思想融合。这也延续了李宏图教授在《札记》中反复提醒我们的洞见:启蒙运动并非一条由理性单向演进的历史之路,而是一场多源并发、相互激荡的思想革命。不同样式的启蒙,虽同以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为旨归,却在思想逻辑、制度基础与历史取向上殊途并进,构成了启蒙思想内部张力的深刻对照。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并存与互辩之中,启蒙运动才真正展现出其创造性,不仅开辟了通往现代政治与道德世界的多重路径,也由此展现出现代性本身多源共生、持续生成的活力。
正如《札记》指出,启蒙思想的研究仍远未穷尽,诸多方向亟待深化,譬如政治经济学在斯密之外的多元思想生成、全球启蒙的跨语境传播与再语义化、启蒙与宗教的关系、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等等。而正如李宏图教授所强调的,在诸多议题的讨论之下,一个根本的认识则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而现代文明正是从‘商业文明’中萌生。”在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伦理图景中,“商”往往被认为“逐利而无义”,经济行为缺乏独立的道德正当性;五四运动以来,“启蒙”更多与“民主与科学”“民族解放”“反专制”等政治维度联系在一起,社会性、制度性与经济伦理层面的启蒙则常常被边缘化。然而,亚当·斯密曾说,再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巴斯夏曾写,“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的全部。”我们惊觉原来“商业”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一整套以交换为基本关系、以信用为核心机制、以法治与契约为制度保障、以同情、公正等道德情感为内在约束的社会结构。在这一视野下,市场与制度秩序、道德规范与知识生产彼此交织,构成现代社会的深层逻辑。
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商业社会”的洞见正在于此。他们将经济合作理解为一种“文明化”的过程,以礼俗与交往训练社群的自治与互信,以市场关联塑造利益的相互依赖,从而为政治宽容、公共协商、科学理性与社会进步铺就道路。他们提醒我们:真正的现代文明,恰恰是在市场、法治与道德的交织中缓慢生成的。而无论是技术的繁荣还是财富的累积,其根本旨归,仍然在于让每一个个体自由、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综观全书,《新启蒙札记》不仅是一部具有学术创见与思想深度的思想史文集,更是一种面向现实的精神回应。它以札记的形式承载学术的厚度,以严谨的考辨与“复数”的视野,为我们拨开了环绕“启蒙”命题的重重迷雾。启蒙的未竟之业,不在于宣告某种普遍价值的终极胜利,而在于如康德所言,保有持续“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勇气与实践。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撰文:李嘉琪;编辑:刘亚光;校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股票股指配资,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国汇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